時間:2022-10-10 14:52:48
緒論:在尋找寫作靈感嗎?愛發表網為您精選了1篇東漢魏晉書評下雕蟲藝術民間化成因,愿這些內容能夠啟迪您的思維,激發您的創作熱情,歡迎您的閱讀與分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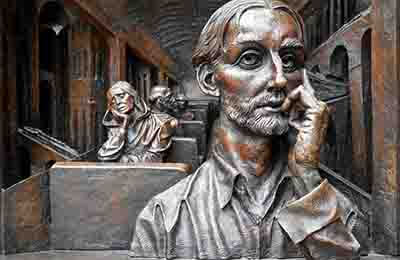
摘要:“雕蟲”藝術是一種極富裝飾性的文字藝術,以對字的筆畫進行形變或添加裝飾為特征。東漢魏晉時期是書法發展的黃金期,多種書體的確立和書法名家的出現,促進了書法理論的發展。該文著眼于東漢魏晉書評,探析“雕蟲”藝術為何日益趨向民間化,即為何逐漸遠離主流書評視域,分析“雕蟲”藝術和主流書評在追求與標準上的異同,探討“雕蟲”藝術民間化對當今書法藝術發展創新的啟示。
關鍵詞:東漢魏晉;鳥蟲篆;花鳥字;書法品評
東漢魏晉時期是書法發展的黃金期,人們對書法的藝術自覺逐漸覺醒,隸書、章草、行書、楷書的出現使文字不再局限于“畫成其物,隨體詰詘”的象形描摹。隨著這些新字體的出現,社會上產生了一批有影響力的書法家,進而提高了人們對書法藝術的熱情。多種書體的確立和書法名家的出現也促進了書法理論的發展,這一時期可看作書法藝術理論的源頭。這一時期的書論思想極富代表性,對后世的書論研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鳥蟲篆起源于春秋戰國時期,漢許慎《說文解字序》中對鳥蟲篆有著這樣的記載:“及亡新居攝,使大司空甄豐等校文書之部,自以為應制作,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即小篆,秦始皇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曰佐書,即秦隸書;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書,所以書幡信也。”[1]從書中記載和傳世器物看,鳥蟲篆是一種裝飾意味較為濃厚的美術字體。這種字體常以鳥、蟲、魚的造型裝飾筆畫,整體繁復華麗,書寫煩瑣,多被用于裝飾器物或防偽。這種美術字體在不同的朝代有著不同程度的繼承和發展:春秋戰國時期青銅器上的鳥蟲篆,唐宋明清時期一些文人、僧侶、官員整理的紙質或碑刻的集篆作品,以及近代的花鳥字。這些都可以看作鳥蟲篆的衍生物。漢揚雄《法言·吾子》中有云:“或問:‘吾子少而好賦?’曰:‘然。童子雕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為也。’”[2]這段問答中提到的“雕蟲篆刻”原意是雕章琢句,“雕蟲”可視為辭藻華美、言之無物的文章的代名詞,后“雕蟲”一詞逐漸代指鳥蟲篆。筆者認為,“雕蟲”一詞不僅可以用來代指鳥蟲篆,而且其形容細膩繁雜的詞意也與上述鳥蟲篆衍生物的特征暗合,故將鳥蟲篆及其衍生物概括為“雕蟲”藝術。簡單來說,“雕蟲”藝術是一種極富裝飾性的文字藝術,以對字的筆畫進行變形或添加裝飾為特征,達到隱喻、祈福或凸顯神秘感等目的。“雕蟲”藝術最早出現于廟堂,有著獨特的藝術價值。但“雕蟲”藝術在后續的發展中處于邊緣位置,難入文人主流視域,最終成為一種民間藝術。筆者認為,這種情況是“雕蟲”藝術難以順應主流書法審美觀念的改變導致的。文章著眼于東漢魏晉書評,從草書地位提升、書法優劣品評標準的初步建立、“三玄”思想對書評的影響等方面探析“雕蟲”藝術為何日益趨向民間化,探討“雕蟲”藝術民間化對當今書法藝術發展創新的啟示。
一、東漢魏晉書評視域下“雕蟲”藝術民間化成因
東漢魏晉時期是中國書法理論發展的初期,其很多思想與品評觀念都對后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這一時期,草書的出現在一定程度上增強了書法的藝術性,書法的象形意味逐漸淡化,抽象內追逐漸成為書家的新追求。東漢魏晉時期,書法的品評標準逐步確立,針對書法本身的結字筆畫、將書法看作有生命力的對象等品評標準,都在這一時期有所體現。當時,在思想領域占據主體地位、以道家經典《老子》《莊子》和儒家經典《周易》為基礎的玄學思想對這一時期的書評也有著一定的影響。東漢魏晉時期,草書的地位逐漸確立。崔瑗《草書勢》有云:“書契之興,始自頡皇。寫彼鳥跡,以定文章。爰暨末葉,典籍彌繁,時之多僻,政之多權,官事荒蕪,剿其墨翰。惟多佐隸,舊字是刪。草書之法,蓋又簡略,應時諭指,用于卒迫。兼功并用,愛日省力,純儉之變,豈必古式。”[3]16草書本是一種民間用于簡便書寫的方法,但在當時經過崔瑗等書家的推崇,逐漸確立了其與篆書、隸書同等的地位,這與草書特有的抽象性是密不可分的。草書的抽象性對應的是圖像性。圖像性是向外的模仿,是對自然界的描摹重現。草書的抽象性可以喚起人們向內的模仿,需要人們通過觀察草書的勢態法象,聯想到自然生活中的“狡兔暴駭,將奔未馳”“狀似連珠,絕而不離”“騰蛇赴穴,頭沒尾垂”“摧焉若阻岑崩崖”。這種聯想型的書評模式也影響了東漢魏晉時期有關其他書體的書評。如:成公綏《隸書體》中,有關隸書“或若虯龍盤游,蜿蜒軒翥,鸞鳳翱翔,矯翼欲去”的聯想;蔡邕的《篆勢》從篆書章法結果聯想到“或龜文針列,櫛比龍鱗;紓體放尾,長短復身”;王珉在《行書狀》中描述優秀的行書應激發人們“宛若盤螭之仰勢,翼若翔鸞之舒翮”“或乃放乎飛筆,雨下風馳,綺靡婉麗,縱橫流離”的聯想。中國古代哲學常將自然中的事物與人的種種行為相對應,書法也是同理。這些書評與自然生活緊密相關,但同時也與自然生活保持著一定的距離,獨立于自然生活的表象之外。同時,草書較為自由的書寫表達更容易契合書寫者的個性、心境。草書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中國人書法審美意識的發展,后世的書論也多是基于這兩點。可以說,草書的出現奠定了中國書法理論重抽象聯想、表情內追的主基調。“雕蟲”藝術是裝飾性文字藝術,相較于正統的篆書,其圖像性更加顯著。不論是鳥蟲篆還是由其衍生出的飛白書、花鳥字,雖然字內裝飾繁復細膩,但本質上都可以看作對外簡單的模仿裝飾。其較強的圖像性和裝飾性基本阻絕了其引發人們聯想或內追的可能,與草書出現帶來的重抽象聯想、表情內追的審美基調并不相符。
這是“雕蟲”藝術逐漸遠離主流書論視域的原因之一。此外,書法的優劣品評標準也在東漢魏晉時期初步建立。當時的書法品評標準大致可以分為:針對書法本身結字筆畫的品評,即文字的筆畫是否精熟、結構是否工巧等;將書法看作一個有生命力的對象的品評,即引入肥、瘦、骨、筋、肉等概念品評書法。針對書法本身結字筆畫的品評和將書法看作一個有生命力的對象的品評,在后世的書評書論中都有所繼承與發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對書法藝術審美對象的選擇。針對書法本身的品評中,精熟工巧是東漢魏晉時期重要的品評標準。徐鍇釋云:“為巧必遵規矩法度,然后為工,否則目巧也。巫事無形,失在于詭,亦當遵規矩,故曰與巫同意。”在東漢魏晉各種書體逐漸確立的時期,需要有人將這些書體規范化、標準化。所以這一時期,精熟工巧是書法品評的重要標準。衛恒《四體書勢》中評價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下筆必為楷則”,對比蔡邕與邯鄲淳“漢末又有蔡邕為侍中、中郎將,善篆,采斯、喜之法,為古今雜形,然精密閑理不如淳也”。王羲之曾在書論中提到“吾書比之鍾、張,當抗行,或謂過之。張草猶當雁行。張精熟過人,臨池學書,池水盡墨,若吾耽之若此,未必謝之”。由此可見當時對精熟工巧的推崇。對于“雕蟲”藝術來說,其表現形式十分精妙復雜。但“雕蟲”藝術的精妙復雜是服務于其裝飾、防偽、祈福、暗喻等功能的,并非為了追求標準化、規范化。所以,雖然“雕蟲”藝術也追求工巧,但很難進入此類書評的視域。通過分析南朝王僧虔的《論書》和唐代張懷瓘的《書斷》,可以窺見東漢魏晉時期以韋誕、衛瓘為代表的另一種書法品評方法:“韋誕云:杜氏杰有骨力,而字筆畫微瘦。惟劉氏之法,書體甚濃,結字工巧,時有不及。”[3]60“崔、杜之后,共推張芝,仲將謂之筆圣,伯玉得其筋,衛恒得其骨。”[3]163肥、瘦、骨、筋、肉的概念源于人們對自身的認識。漢代,通過觀察一個人的身體特征即可推演其命運的說法已經十分流行。將骨、筋的概念引入文藝批評的是當時的書法理論。這里提到的肥、瘦、骨、筋、肉的概念,是將書法本身看作一個有生命、有靈魂的審美對象,通過骨、筋、肉的概念描述書法外顯的輪廓(肉)和其內含的生命力(筋、骨),通過肥、瘦的概念概括不同書家書法作品顯露出的氣質(圖1、2)。在“雕蟲”藝術中,不論是鳥蟲篆、唐宋明清的一些集篆作品還是花鳥字等,其本身更多的是對于其他事物的模仿或象征,故難以用肥瘦的概念概括。而且因其表現載體、創作目的、作者水平等原因,“雕蟲”藝術也很難用骨、筋、肉的概念形容其生命特征。
東漢魏晉時期,以道家經典《老子》《莊子》和儒家經典《周易》為基礎的玄學思想逐漸成為思想領域的主流。這種思想在以道家思想為主體的同時,輔以部分儒家思想,對當時的書法審美產生了一定的影響。道家經典《莊子》中記錄了莊子與惠子的“濠上之辯”:“莊子與惠子游于濠梁之上。莊子曰:‘鰷魚出游從容,是魚之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4]在莊子的世界里,他與魚是沒有分別的。在濠梁之上游玩的莊子,就是那條悠游地穿行于世界之河的魚。可見道家的思想是一種更抽象、更具詩意的思想,強調會通物我,大道不割,打通世界與我的界限,通世界以為一,以無分別的心態體驗萬事萬物。《易傳》中提到的“生生之謂易”,即新變與創造,是儒家的核心思想之一。儒家注重創造,在儒家的視域中,世界是創造變化的,所以創造變化合乎天道。張彥遠的《法書要錄》中記載王羲之有云:“須得書意轉深,點畫之間皆有意。自有言所不盡。得其妙者,事事皆然。”“子敬飛白大有意。”王羲之提到的“意”不能簡單地用字形結構概括,而是一種更抽象的品評概念。書法本身就具有打破界限、會通物我的潛力。玄學思想的流行促使當時的書法批評有了從關注文字的“象”轉變到關注書法的“意”的傾向。同時,文字本身就是先民對自然形象的高度概括與創造,書法又因不同的功用目的、工具材料、結字與用筆技巧、審美取向、氣質個性等,得以在文字的基礎上再創造。書法作為抽象藝術,也容易表現意境和審美觀念。“雕蟲”藝術的關注點大多停留在其外象,較少關注內層的意境。其繁復的造型與較強的裝飾性,也阻斷了以抽象的筆畫結構會通物我。對于“雕蟲”藝術來說,其創造自作品完成之時就已經結束了,難以更進一步地表現意境。所以從這一點看,“雕蟲”藝術與主流書法的審美標準尚有一定的差距。相比于東漢魏晉書評的標準,“雕蟲”藝術與民間藝術更為契合。民間藝術是相對于文人藝術、宗教藝術等而存在的概念。民間藝術多采用象征、借喻、抽象、夸張的造型手法達到求吉納福等目的。不難發現,民間藝術的表現手法基本停留在對外形的改變上,這與“雕蟲”藝術的特點相契合。由此可知,“雕蟲”藝術有較強的圖像性和裝飾性,與東漢魏晉草書帶來的重抽象聯想、表情內追的審美基調并不相符。又因為“雕蟲”藝術的精妙復雜不利于追求標準化、規范化,所以“雕蟲”藝術很難進入東漢魏晉時期追求精熟工巧的書評視域。而且“雕蟲”藝術的關注點大多停留在外象,難以適應書法藝術隨著各種思想的影響愈加強調內追意境的趨勢。因此,“雕蟲”藝術在歷史中逐漸遠離主流書評視域,并日益趨向民間化,成為民間藝術的一部分。
二、“雕蟲”藝術民間化成因的啟示
通過分析東漢魏晉書評,不難發現書法在這一時期逐漸發展為方便、實用且能寄情遣興的符合文人理想的藝術形式,并對書法未來發展的大趨勢(即注意力從象形逐漸轉向寫意)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東漢魏晉時期是書體形成期到書家個性發展期的過渡階段,這一特殊時期促使書法藝術的審美對象發生了改變,書法理論研究也在這一時期初見成果。這一時期,“三玄”思想盛行,文人對藝術的思考不再僅僅停留在外部裝飾上。這些因素的綜合結果是東漢魏晉產生的書法字體愈加擺脫象形性,并逐漸向抽象性方向發展。這一時期的書法審美也逐漸從外形裝飾轉向意境、精神等方面。這種現象追根溯源是由最早的中國文字的象形性帶來的審美意味,加之文字實用性發生的演變與各種思想文化的發展綜合作用的結果。但反觀“雕蟲”藝術,其起源于春秋戰國時期,最早是古代上層階級的產物,也是一種裝飾意味較為濃厚的美術字體。這種字體常以鳥、蟲、魚的造型裝飾筆畫,整體繁復華麗,書寫煩瑣,多用于裝飾器物或防偽。這種美術字體在不同的朝代有著不同程度的發展,但都可以看作鳥蟲篆的衍生物。“雕蟲”藝術主要通過改變字的外形表現創作者的隱喻、祈福心理,或以凸顯神秘感等為目的,難以適應東漢魏晉時期書法審美的變化,因而逐漸遠離了文人書法視域。但是,“雕蟲”藝術的特點與民間藝術多采用象征、借喻、抽象、夸張的造型手法達到求吉納福等目的的特征高度吻合。而且“雕蟲”藝術和民間藝術都是通過對表象的改變重組實現相應的創作目的,故“雕蟲”藝術在后續的發展中逐漸進入民間藝術的范疇。當代書法在發展過程中尚有一些重形式、輕意境的趨勢。筆者希望能通過分析“雕蟲”藝術民間化的成因,促進書法向更好的方向發展。
參考文獻:
[1]崔爾平,校.歷代書法論文選續編[M].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17:9-10.
[2]管南海.“雕蟲小技”獻疑[J].藝術品鑒,2018(23):64-66.
[3]黃簡.歷代書法論文選[M].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14.
[4]朱良志.中國美學十五講[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24.
作者:蘇國瑞 單位:江蘇師范大學美術學院